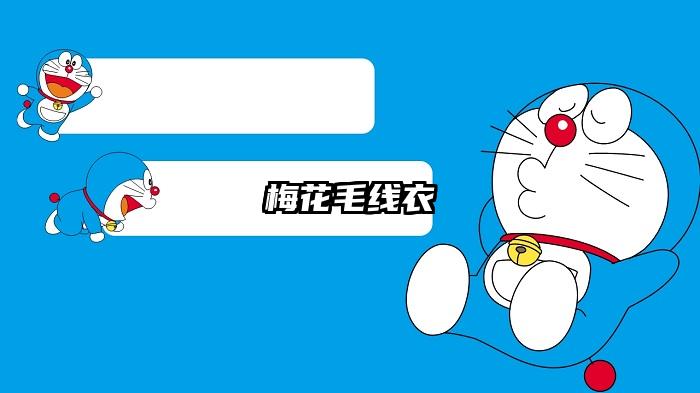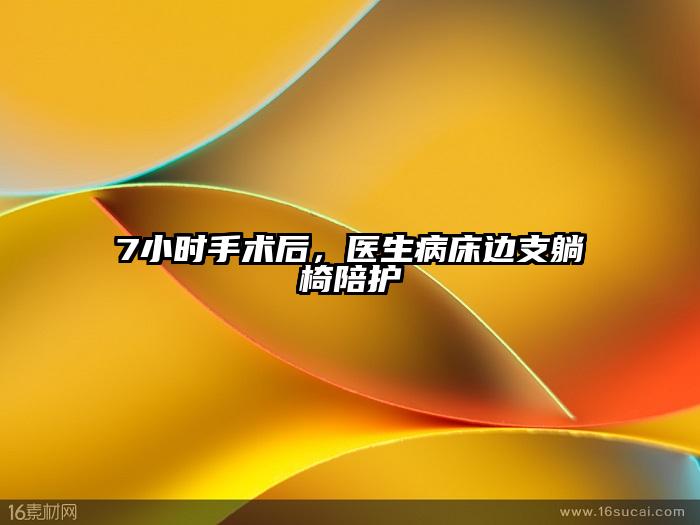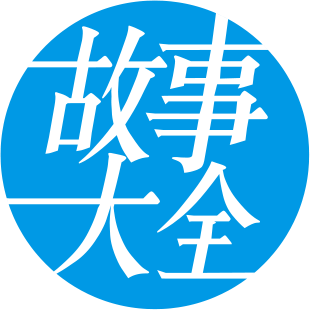最后的温暖谁来给
在生命的最后280天,我们如同回到出生前的模样,娇弱、敏感,但又比新生命多了疼痛、不甘、留恋。如果生不能由自己选择,那能以安详满足的表情阖眼,也许是在生命终点的最后心愿……
每天都在拥抱死亡的人
徐丽躺在病床上,肺癌晚期,不能喝水、不能吃饭,痛是连进入睡眠都摆脱不了的恶魔。最痛时,徐丽仿佛恍惚间看到了死神的影子。也是在那天,儿子李勇突然握紧她的手:“妈,我给你转院吧。”李勇把母亲转到了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母亲爱美,一辈子没吃过苦,“我不想浑身插满管子,大小便失禁那样丑陋地死去。”徐丽对儿子说。
临终关怀是什么?即便把母亲送到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李勇依旧不清楚它的全貌。“它能让生命变得有尊严,有价值。”医院创办人,65岁的李松堂说。松堂医院创办28年间,共送走了3.2万名病人。“有一天我死了,希望墓志铭可以写上:‘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在拥抱死亡。’”
临终关怀的目标是优逝,即为生存时间在3~6个月间的患者提供姑息治疗,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尊重病人的意愿,并对病人家属提供心理安抚。“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欢快的歌,我不希望这首歌以悲伤的曲调结尾。”
生命最后的诉求
临终关怀的第一层是以减轻疼痛为主的姑息治疗。在家属看来,松堂医院是国内为数不多配备专职医生的“养老院”,他们能提供止痛针、阻断疼痛神经手术等多种方式帮助病人止痛。
临终关怀的第二层是满足病人的心愿。松堂医院的工作人员会给老人举办“个人演唱会”,给一直嚷着要加工资的脑萎缩病人“发工资”,为聊得来的两位痴呆老人举行“婚礼”。而且家属能随时来探望、陪伴,没有限制。
第三层则是让那些即将跨入天堂的老人,找到人生尚存的意义。每天早上10点,张文成都会坐在钢琴旁弹一曲。由于盆底神经和腰神经损伤,他的腰部以下无时无刻不在疼痛。因为太痛,他自杀过两次。后来他看开了,“既然命运这么安排,就坦然面对。”上午唱歌弹琴,下午写诗,他找回了7年前的生活节奏。
在李松堂眼里,病人们就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他把一楼活动大厅布置得如同幼儿园,黄红绿的彩色墙上挂满了千纸鹤和毛绒玩具。“生命怎么来,就让他们怎么离开吧。”
理论上,临终关怀机构不等于养老院,但国内大部分以此为主要营运项目的私立医院,都尴尬地接受了自己沦落为养老院的窘境。李松堂接收的大部分病人都在松堂医院住满6个月以上,长的,已经在这里待了3年有余,“家属每年打一笔款,但我们已经联系不到他。”
越害怕死亡,越需要最后的慰藉
松堂医院曾尝试搬进社区,第一次搬迁即遭到上百名居民的围堵,他们吼着:“这么多人来这里,说白了就是等死。”医院里的老人们无处可去,在马路边上坐了4个多小时。
松堂医院成立的28年里,搬过7次家,如今的落脚点是北京东五环外的京通快速路旁。医院在辅路上,离居民区有些距离,120或者999的车来尽量不鸣笛,出殡的车有时也不挂黑纱。把死亡气息降到最低,是他们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
根深蒂固的“孝道”则在临终关怀与病人间架起更多阻碍。2015年1月,上海浦东机场社区卫生中心首次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舒缓病房”。为了营造舒适的氛围,病房装修时选用了淡紫色窗帘、鹅黄色地板、原木色橱柜,如在家里,但连续几个月病房空置率都极高。
一次,一位年轻人带着肺癌已转移的老父亲来看病房,房间的装修让他好感倍增。可当护士向儿子传达了“临终关怀”的理念后,对方的脸色变了:“总的来说,就是等死对吧?你让我回家怎么做人?”治疗,无论是有效还是无效,才是子女尽孝的证明。
但是,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认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的年轻人目睹亲人临终前的苦痛后,已经开始主动了解临终关怀。
除了李松堂他们,也已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临终关怀。
1998年,在探望一位罹患癌症的朋友后,李嘉诚开始关注临终关怀。此项目命名为“‘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免费为内地贫困的晚期癌症患者提供各方面的照护。在项目官网上公布了相关数字:“项目开展逾15年,已为13.5万患者解除了痛苦,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到心灵的慰藉。”
路还很长,让每个人在生命尽头都选择优雅离开的理念,已悄然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