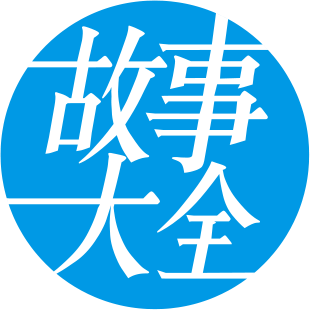作为他山之玉的宇文所安
近年,费正清、高罗佩、顾彬、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王斯福、崔瑞德等汉学家的著作已寻常可见,宇文所安异军突起,尤其是他散播的唐诗流韵深入人心,包括2012年由三联书店推出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行家也赞叹不已。

一个人一生的安排,也许就是源自一次刻骨的“相遇”,在洋人看来,就是一次洗筋泛髓的神启。宇文所安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来自中国的古典诗词魅力在他幼年的阅读时光中翩然君临,自此欲罢不能,沉迷其间,以至于他父亲担心他的研究嗜好会让他饿肚皮。但宇文十分聪颖,他由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者逐渐成为了一代大家,这不能不归结于他的高度敏感,他善于在范式里发掘异样的情愫,并从庸常的见解背后提炼出卓见。这就意味着,宇文不仅仅是敏感的,他更有在邈远山水、草木当中感知诗者命运、悲欢、沉浮的古典情怀。在我看来,宇文已经金钩银画,是汉语的宇文所安,这很容易让我们模糊那个遥远的斯蒂芬·欧文。
宇文从1973年出版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以来,他的研究领域从作家研究推向诗歌史、诗歌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开始对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予以全方位考量。随着他的《追忆》《迷楼》《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以及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先后在大陆翻译出版,赞美之余,让我们发现他治学重心的最显著变化,是从“诗史”到“诗学”的挪移。他在古典氤氲中的转身,还让学界中人深切意识到,“一位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除了勤奋和颖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不断的反省能力,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研究类型和自身能力两方面的局限,并对成功的模式具有高度的警觉和随时准备摆脱它的决心。”
诗人就是世界的命名者。因此,说出就是照亮。基于对现实的难以言说,因而今天的诗人们正在失去命名的能力,但总有人试图恢复诗人往昔的光荣。记得我最早阅读宇文的作品是《迷楼》。书名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命名,正如它的副标题“诗与欲望的迷宫”所显示的,是诗歌中对欲望的呈现。诗歌是欲望的语感,而欲望几乎就是诗歌的语境。用迷宫对应于西方诗歌,用迷楼来指称中国古典诗词,可谓相得益彰。对这样一种命名风格的偏爱甚至迷恋,在宇文所安来说已是根性。
迷宫里的事物总是被赋予了超现实的光晕。当代中国人对迷宫产生迷恋,主要是源自置身庞大图书馆和时间深处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认为迷宫根本没有出路,那些错综复杂的“假路”,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可能,但世界即在迷宫之中。其实在希腊神话里,米诺斯迷宫就成为了一种极端复杂的隐喻。忒修斯到了米诺斯王宫,公主艾丽阿德涅对他一见钟情,公主送他一团线球和一炳魔剑,叫他将线头系在入口处,放线进入迷宫,忒修斯在迷宫深处找到了米诺陶洛斯,经过一场殊死搏斗,终于杀死了米诺陶洛斯。可见,这是一个有解的迷宫,是一个有出路的迷宫,理性主义的睿智洞悉秋毫,迷宫不迷,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线性迷宫”。
那么,中国式的迷宫——迷楼,是否有解?或者对有些人来说,迷楼正是保护自我的超级堡垒。
“迷楼”原指隋炀帝在7世纪初建造的一座供其恣意享乐的宫殿,其本义就是“让人迷失的宫殿”。无论是谁,只要进入迷楼,就会迷而忘返。在我看来,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力走出迷楼,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愿意出去。那么,无论作为时间纠结的迷楼还是作为空间回环的迷楼,作者似乎忽略了有关迷楼的另外一个说法:唐代颜师古的《大业拾遗记》记载说:“帝尝宰昭明文选楼,车驾未至,先命宫娥数千人升楼迎侍。微风东来,宫娥衣被风绰,直泊肩项,帝睹之,色荒愈炽,因此乃建迷楼。”此乃目迷五色之“迷”,色迷迷,更多体现了迷楼的情色空间性质。尽管如此,宇文用以打量迷楼的手电筒,就是隐喻。
正如《迷楼》的翻译者程章灿先生指出的那样,宇文对两类系列的隐喻情有独钟:一个是有关行走、路途、岔道、迷路之类的隐喻,如《绪论》中提到的临阵脱跳,第一章中的离开爱尔兰、进出于舞圈,招引走上歧路、岔道,第二章中的牧女与蚕娘的途中遭遇、陌路的荡子,《结语》最后的走向他方,等等;另一个是有关建筑的各种隐喻,如第一章中的“马拉美内室”,第三章中的“相邻秘室,“里尔克之室”,第四章中的“回廊”,第五章中的“前厅”,《结语》中的“假出口”、“此路不通”等。可见,书名中的迷楼和迷宫不仅隐喻本书的论述对象,也同样隐喻本书的结构特点和论述方式,是兼具客体和主体双重指向的隐喻。这里凝集了作者的精细和深微用意。
那么,以隐喻照亮隐喻,以修辞的隐喻来“澄清”认知的隐喻,也许会让事情进一步“迷楼化”。中国古典诗歌表达的远不止是一种人生/写作经验,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诗歌还揭示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它帮助个人确定他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当然,作为纸上迷楼的建筑者,宇文可能比读者更清楚一个用意:他在以“隐喻诠释学”行走于诗歌中,他留在诗歌巷道中的身影,也是一种隐喻。这就像一个古物的修复者,他的复原主义努力,恐怕也有不少粉饰成分。这自然让我产生了如下臆想:古人的诗文,真有如此繁奥吗?
宇文所安作出了一种富有生机的解释,意味着他给出了一种他的理解。这姑且叫做“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尝试“抛开固定的期待”,经常给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颇有启迪人心之处。宇文所安实际上将古典文学中的作家还原成了具备普遍人性的普通人——《回忆的诱引》对于李清照之潜在的怨恨情绪的发掘,将这种还原推向了极致。所以,《迷楼》的成功,不在于提出了什么观念结构,而在于这些诗歌经过他的复原,给我们带来了簇新的愉悦。
宇文所安的作品文笔卷舒,开合自如,所谓深得事物中元的抒写,在宏大叙事为主导的学院派话语中别具一格。他所偏爱的“文本细读”,最为和洽的言路,就现代汉语而言,更应归属于随笔,而不是散文。
所谓“真正的断片,是举隅物,是时间的宠物。”宇文所安认为《论语》储存了大量的断片,没有说出来的话远远多于说出来的话,“当你能够从只有经验丰富的眼睛才能勉强辨认出的地方,得到作品的表明拒绝提供给你的那种智慧和深沉的感情时,你就得到了为‘含蓄’设立的奖品。”其实,断片正是汉语随笔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断片并非碎片,更非整体的碎屑。断片是对思想的深犁。从高处着眼,断片就是个体思想者逾越天堑与宏大叙事的一根钢丝。常识告诉我们,思想必须通过它最“对位”的文体来表达。文体之变,宛如兵器之于技艺的重要。显然,文体意识是由文本在读写过程中的自有功能所决定的。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为写作提供了编码程序;为阅读暗示了解码方式。我再提示一个如下的言路:思想往往是在思者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光临的,它总是以缓慢的姿态出现,让思者松弛下来,准备好盛接它的器皿。它以一个形象、一个反诘、一个断片的彰显来还原我们渴求的形象。时间被劝化了,空间柔软而浑圆,思想得以打开,使黑暗进一步黑下去,黑得雪亮;思想使光进一步纯粹,就像刃口上飘过的细雪......
宇文所安超拔于庸常研究的言路和精深,为汉语文学打开了簇新的视域。这意味着并非读书人都可以自称为“读者”,必须是如宇文所安的词语“追忆”,才称得上是“读者中的读者”。退到文字深处的古人,他们的文字,其实就是为宇文所安这样的人而准备的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