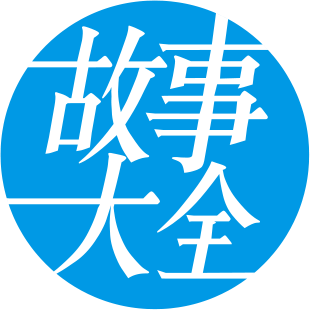聊斋故事之人鬼情缘
一
诸暨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草塔镇北面的平阔,一个是位于牌头镇东面的狭山。从字面上理解,平阔是又平又阔,而狭山是又狭又小。实际上呢,是“平阔勿阔,狭山勿狭”,地势与地名刚好相反。今天所讲的人和鬼,就发生在狭山,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二
狭山者,两山之间一长溜的开阔地也。靠北的山脚边,蜿蜒大路与越山溪并行,通向长坛老街。中间,喜鹊尾巴岭越过山岗,岭与路交界处坐落着“狭山亭”。凉亭很普通,就是乡村里常见的那种,白墙黑瓦两门对穿,亭内靠墙砌着两排石凳,供过路客歇息。
东南方向是个大村子。早先,村里有个杀猪之家,父亲姓楼名富,年轻时身强力壮,两三百斤的猪,一个人就能拖上杀猪凳,白刀进红刀出。近年来上了年纪,体力眼力都不如从前,就把技术传给了儿子楼裕,自己在家饲鸡种菜,或者与老婆一起去庙里拜菩萨,祈求儿媳进门,早日抱上孙子。楼裕二十出头的年纪,长得高大挺拔,身体结实得像山上的岩石疙瘩。
不管是现在还在过去,杀猪总是赚钱的行当,所以楼家的生活很小康。这样的后生这样的家境,媒人是踏破了门槛,可楼裕从来没去相过亲。这事说起来,就要怪村头的山爷爷。
三
山爷爷是孤老太公,住在村头的祠堂里。他记性好,早些年在外贩牛贩羊,到过的地方多,肚子里全是前朝后代、稀奇古怪的事。要是听他聊起天来,男人不要出畈,女人不要烧饭。楼裕小时,常与村里的伙伴一起来到祠堂,听山爷爷讲七仙女配凡人、狐狸精配书生、前世盖衣定姻缘等等。像现在传销洗脑一样,听得多了,心里就入了迷。以致成人后,当父母催他去看姑娘时,他就说:“婚姻全凭天意,缘分没来时,天天看也没用。缘分来了,漂亮姑娘会拉着我的手,甩也甩不掉。”
父母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天下无媒不成亲,哪有姑娘自己上门来的?后来想想,儿子要杀方圆十里的猪,本村邻村,齐正的姑娘多着,说不定真有自己看中的。如若是这样最好,以
恐怖鬼故事第四个人
后居家过日子夫妻相吵,省得埋怨媒人和父母。四
外村有户人家办喜事,这天晚饭后,楼裕给他们杀了两头猪,等到收拾完毕回家,已经是半夜前后了。月亮很好,走在路上,能看清楚山上的树和毛竹。四周很静,人们都进入梦乡,偶尔传来田鸡和夜莺的叫声。前面就是岭脚了,忽然,楼裕看见有个白影子,闪进了凉亭里面。这么晚了,谁还在外面游荡?会不会是偷东西的贼?楼裕是杀猪的,胆子本来就大,决定进去看个明白。
拐了个弯,走到凉亭里面,见角落站着一个女子,身材高挑,穿着宽荡荡的白上衣,头发散散的披在脑后,一袭黑长裙拖到地上,盖住了双脚。看来是两口子吵架,赌气走出来的。
楼裕走上前去,说道:“你位阿嫂,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在诸暨民间,未出嫁的女子喊大姑娘,一旦嫁了人就喊嫂嫂了。如果大姑娘你喊了嫂嫂,是对人家不尊重,哪怕是错口出,她也要翻脸骂人。这不,楼裕无意间一声阿嫂,那女子就来气了,她转过身,眼睛一瞪喝道:“闭上你的臭嘴,你妈才是阿嫂,本姑娘清清白白,滚开!”
好大的火气啊!楼裕一时怔住了,不知如何应对是好。月光斜照在地面上,亭内亮堂堂的。两人面对面站着,可能是刚才气的吧,或许是反光的缘故,姑娘瓜子形的脸孔白得像一张纸,几乎没一点儿血气,一双乌黑水灵的眼睛倒很好看,嘴巴也长得小巧玲珑。要是脸孔红润一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啊,楼裕想起了山爷爷所讲的仙女,不禁一阵心动。
见后生被呛得脸孔红红,姑娘感到自己言重了,嘴角露出了歉意的笑容。楼裕呢,觉得这样离开心不过安,万一遇上山匪兵匪,姑娘岂不要遭殃?于是继续劝说道:“你一个人出来,父母肯定着急了。家住哪里?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后生如此热心,姑娘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人家这么真诚,如果自己不声不响地走开,说不定他会尾随而来,与其让他跟着,还不如大方一点回答,省得他起疑心。再说,后生阿哥五官端庄,阳刚之气十足,很有男子汉的味道呢。于是,姑娘指了指亭
小孩子能看恐怖片鬼故事吗
外,开口道:“我家就住在反山,没多少路,翻过岭岗就到。这里溪水清亮,环境清静,有月亮的夜里,我常沿着山路走过来。小阿哥若有时间,明天月鬼故事带图超恐怖
亮升起来的时候,来陪我一起散步吧。”从来没有姑娘如此主动来相约,楼裕一时呆住了,竟忘记了点头应答。姑娘说完,甜甜地一笑,飘然出了凉亭,走上了长长的山道,等楼裕回过神来,她已拐入山湾不见了影子。楼裕心中好有些失落,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眼晴睁开,一忽儿是仙女,一忽儿是狐狸小美女,眼睛闭上,仙女与小美女重叠在一起,变成了白衣姑娘。
五
楼裕杀猪,从来都是“一刀清”,干脆利索。第二天,他心神不宁,总惦记着与白衣姑娘的约会,以致一连捅了三刀,那头猪还唱着“高调”。没办法了,见旁边豆腐桶里汤水正满着,就后脚一提,把猪头沉入水中,溺死了之。
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楼裕饭碗一放,打扮一番,出了村口匆匆来到岭脚。白衣姑娘已在亭中等候,见楼裕到来,满脸荡漾着舒心的笑意。今天,她穿了一件淡蓝色上衣,一件白色的长裙,清爽整洁,如一朵含苞的百合花。此时,月明云淡,微风吹拂,溪流淙淙,姑娘在前,楼裕紧跟在后,两人沿着大路慢慢踱着步。气氛有些紧张,楼裕心跳得厉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姑娘打破了僵局,操着甜软的口音,自我介绍了起来。
姑娘姓萧名慧,老家在水乡扬州,那里湖水如镜,杨柳如烟,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然而,邻近的长江,每年总要发几次大水,田园一片汪洋,人们只好背井离乡去逃荒。五年前,萧父夫妻带着她姐弟俩,来到了山那边的小村。父亲学过医,常给附近村民看小毛小病,母亲与她刺绣香囊,或送给村里的小孩佩戴,或去街上售卖,日子过得还算如意。
楼裕告诉她,自己是杀猪的,每天走东村穿西村,要结果好几条性命,可别怕啊。萧慧咯咯笑着说,猪吃吃睡睡不干活,养大了就该杀,这是上天罚定的,只要你不害人就行。萧慧开朗活泼,善解人意,说话极具吸引力,楼裕的身心一下子放松了。
青年男女一旦情相投,就有说不完的话,而且会越靠越拢。开始时,楼裕与萧慧是一前一后走着,没过多少时候就并排了,最后坐在了溪边的岩石上。话题也很宽泛,乡土风俗、童年往事、兴趣爱好等等。萧慧像一只山雀,话头一扯开就没完没了,似乎好多天没与人说话了,楼裕只有当听众的份,偶尔插上几句。
这世界上,有两件事做起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一是赌博,二是谈情。不知不觉间,月亮已滑到了头顶,该回去了,楼裕想送萧慧一程,萧慧说,左右邻居看见不太好,放心吧,不会出事情的。
月夜相会,过去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据说还会上瘾。别人不知道,楼裕和萧慧就是这样,一发而不可收。每晚,双双踏着月光而来,溪边大路田埂小路,留下脚印一串串。男女相爱,免不了牵手挽臂,肌肤相碰。那天,大概是阴历二十左右,月亮升得有些迟,也有些残缺。两人走了一段路,便坐在山脚边的草地上。
突然,山上传来了尖厉的惨叫声,同时柴草乱动,有活物在竭力挣扎。楼裕知道,是山爷爷摆着的“夹头弶”,夹住了一只小野兽。萧慧吓得抱头躲藏,楼裕张开双手,顺势把她揽到怀里,紧紧地搂住。可能是受了惊吓吧,萧慧的身子冰凉刺骨,没一点热度,好像冬天的蛇一样。楼裕的胸膛原本就火热,此刻抱着美女,更是满腔热血沸腾。冷热相融,萧慧一动不动地紧贴着,温柔得像一只小猫。
六
山爷爷七十多岁了,筋骨还很硬朗,擅长在柴窠蓬中设弶捉兽。那晚,他捕获了一只角麂,也看到了楼裕抱着一个姑娘。第二天,楼裕从祠堂门口走过,山爷爷把他喊了进去,围绕着萧慧姑娘,问得萝卜不生根,葫芦不长藤。
问完了,停了一会说道:“这姑娘来路有些不正。你想想,青葱十八,哪个姑娘脸孔会没有血色?半夜三更,哪个女孩会独自一人爬山过岭?食烟火
张震讲鬼故事恐怖吗?
饭,哪个活人会冷得冰阴激骨?”与萧慧的交往,脑子里全是对方的好,山爷爷所问的,楼裕是压根儿没有去想过。现在一经提醒,尤其是最后一句,越想越是心乱如麻,阵阵发寒,难道萧慧是……不!萧慧不可能是阴鬼,她是活生生的姑娘!见楼裕眼里没一点儿疑惑,山爷爷微微摇着头,心里直感叹,真是一个痴情汉啊!他把楼裕叫到里屋,拿出一个白线团,嘴巴附在楼裕的耳边,如此这般地交代着。
七
男人的胸膛,生来就是让女人依靠的,这话不假。夜里一见面,萧慧就往楼裕的身边挨,一副小鸟依人之态。山爷爷真是神志昏糊,如此温柔可爱,怎么会是脏东西呢?脏东西是青面獠牙,是绿眼睛红头发,萧慧是标准的良家少女啊!楼裕不想去外面,而是抱着萧慧坐在石凳上。荒郊野外,一对痴男情女相拥了,心冲动难控制,免不了唇吸舌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第一次,楼裕是心跳如鼓,手忙脚乱,萧慧是呼吸急促,哼声阵阵。
不知不觉夜已深,萧慧挣脱了楼裕的怀抱,起身整了整凌乱的衣衫,说时间快到月尾,没月亮走山路不便,这几天家里也有一些事,要忙一阵子,下个月的十五,月亮升起时再相见吧。楼裕站了起来,手触到了袋里的线团,想起了山爷爷的话。既然带来了,就试上一试吧,乘萧慧不注意,楼裕把白线缠在了长头发上。
八
第二天上午,楼裕穿过凉亭,爬上了喜鹊尾巴岭。这岭,小时与伙伴们玩“捉强盗”的游戏,曾爬过几次。多年不来,路样没多少变动,只是有几处被暴雨冲毁,露出了横七竖八的乱石。夜里,萧慧来往行走,要是不小心勾上一脚,滚落悬崖如何是好?楼裕直怪自己太粗心。路旁柴茂草盛,鸟语花艳,楼裕没心思欣赏山景山色,只顾低头看路。昨晚,线团放出的白线,跟随萧慧一起回了家。
白线的那一头,就是萧慧的家。马上就要见面了,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萧慧一定会又惊又喜,说不定还会拉到门后,亲上几口呢。可到底是怎样的家呢?一想到这,楼裕的心情沉重了起来。
翻过岭岗,下坡路走起来省力了许多,没多时就来到山脚。山脚边,坟头布满得像钉鞋齿,有新的有旧的。忽然,楼裕看到了白线,沿着小路穿过草丛,拐了几个弯后,钻进了一口护丧棺材。在诸暨农村,人死后大都不是直接下葬,而是将棺材在野外摆放几年,上面盖稻草。此时,楼裕像打着了一记闷雷,一动不动地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待神志慢慢清转,便来到棺材后头,见档板上写着:爱女萧慧之灵柩。
楼裕脸孔铁青,脚骨发软,强打起精神,走到一株大树底下,背靠树身,坐在蛇一样的树根上。没过多时,一位老太太出了村口,拎着竹篮,径直来到萧慧的棺材前,拿出年糕、豆腐等几样供品,一字形摆开。接着,又是点香又是烧纸,嘴里还不停地念念有词。老太太有一大把年纪了,说的又是正宗诸暨话,不像是萧慧的母亲。那她是萧慧的什么人?今天是什么日子?萧慧的家人在哪?楼裕肚里的疑团一个个。
祭祀完毕,见旁边丢着一个树头,老太太想拖回去当柴火,哪知树头大得像箩伞,拖了几脚停下了。楼裕见状,快步走了过去,双手一擎就背到肩上,说刚好要去村里。
有人来帮忙,老太太是眉开眼笑。一搭两便,走路聊天,楼裕指了指背后,兜出了心中的疑团。老太太告诉楼裕,今天是萧慧三周年的祭日,萧慧死后不久,父母及阿弟就回扬州老家了。她是萧慧原先的邻居,萧慧生前,待她像自己的奶奶一样,因念萧慧的好,一年之中的几个要紧日子,都要来坟前看看她。那萧慧是怎么死的呢?老太太一声叹息,抹着眼睛说了起来。
萧慧人俊手巧,做出来的香囊式样多,有的像菱角,有的像桃子,里面包着不同的草药,挂在身上能治病。拿到街市上,身边常常围满人,当然,有一些人是来看好相貌的。
黄勾是一个“破脚骨”,三十多岁了还打着光棍。每日里,常与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寻事打架坑蒙拐骗。见“扬州妹”长得像仙女,他眼睛红起,口水流得像打桐油。那天散市后,他在半路上拦住萧慧,厚着脸皮说,要与萧慧拜堂成亲,如果不同意,就做一场露水夫妻。萧慧表面上柔弱,其实是一个烈性女子,黄勾说话没分寸,她板起脸孔,着着实实地骂了一顿。
恶人总有恶办法,一计不成,黄勾就又来一计。他叫手下的狐朋狗友前街后院去散布,说是“扬州妹”与他上过床,还打过胎。谣言像雾又像风,很快就传播了开来。人们知道黄勾的行径,好多人是摇头不相信,但也有人跟着起哄,当着萧慧的面,说着不冷不热的风凉话,有的甚至指指点点。舌头底下压死人,一个黄花闺女哪受得了这蜚短流长啊?一时想不开,投进了村前的水井里。
原来是这样啊,难怪那次初次相见,自己喊了一声“阿嫂”,萧慧当即发了怒。把老太太送到家,楼裕从原路返回,远远看着萧慧的棺材,心像刀割般难受。这里,萧慧是异乡异客,举目无亲,寂寞之时,灵魂便在月光下出来游荡。如今,自己已深深喜欢上了她,难以分离,不能让萧慧再做孤魂野鬼,她应当过幸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