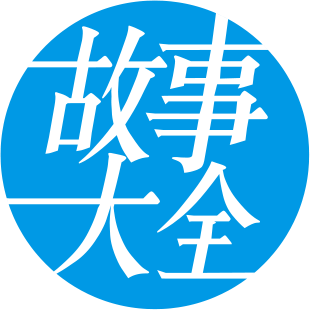母亲缺席的晚餐
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饭桌,我对儿子千呼万唤。小家伙吃饭总是不情愿,我多次唠叨,连儿子都背过了我的台词。他吃着饭说:“妈妈,你小时候能吃上馒头就最高兴了?”
我点头,一边装模作样将饭菜嚼得喷香。我一直是个好养活的人,从不挑饭食,饭菜不管怎样都能吃得饱饱的,终于把自己吃成胖子,现在还得狠心减肥。就算我只吃根黄瓜做晚餐,也尽量坐到餐桌上,慢慢陪小家伙吃完饭。每每此时,就忆起童年,母亲缺席的晚餐。
我童年的餐桌,只留下了数次晚餐的记忆。那时候父亲在公社驻地上班,每天我们起床的时候,父亲已经骑着他笨重的自行车上班去了。一张餐桌上摆着热粥和地瓜饼子,母亲也不坐到炕上来,站在炕沿边,匆匆吃完饭去上工。我们小孩子也跟着急匆匆喝一碗南瓜粥,或者直接抓块苞米饼子拎过书包去学校。午餐常常是不做的。夏天,母亲说,热饭,吃起来麻烦,还把屋子烘热了;冬天,母亲说,天短了,也不干什么活,一天三顿饭吃不开,只把早晨吃剩的饭盛在厚厚的黑泥烧盆里,用包袱盖了,塞进炕头的被子底下,中午时候尚微温的。中午放学回来,各自伸手进去摸块饼子地瓜,去酱坛子里撅点酱或者找棵葱剥了皮就着吃。或坐在炕沿上或站在炕前、灶间,甚至很多时候举着饼子就上街看人家跳房子去了。
只有晚餐的记忆,温馨而隆重。母亲早早淘洗地瓜,和好金黄的苞米面,偶尔也和些白面。切大半棵白菜,珍稀的花生油洒在白菜山顶。间或还炖一碗咸菜条,或者奢侈一点,是鸡蛋墩酱。小干鱼通常不下锅,停火后,在灶膛的微红炭火上轻轻燎烤,鲜香慢慢盈满屋。
父亲常常会倒点酒,自己半杯,母亲小半杯。但是母亲的小半杯酒一直那样放着。母亲缺席着我们的晚餐。她把热腾腾的丰盛晚餐端上炕桌,催促我们趁热吃,她自己却在灶上刷锅,给圈里的猪搅拌猪食。我们小猪一样呼噜噜吃得香甜,等母亲上炕的时候,餐桌上几乎就剩些菜汤,还有横七竖八几根鱼骨头,毛刺刺的鱼鳞。母亲随手端上来一盘昨天或者早上的剩饭,她将颜色暗黄的窝头、饼子捏碎了放进菜盆,倒些热开水进去,成了半盆泡饼子。母亲端起父亲为她斟的酒,就着桌上那几个鱼头,津津有味地吃饭。

父亲的表情很难琢磨,有时候叹气,眼睛望着屋脊说,饭都凉了。母亲说,加点水正好,我吃不惯热饭。母亲接着数落说,这是谁,吃得这样不干净。一只柳叶鱼只刮掉了鱼鳞,吃掉了边刺,鲜美的鱼肉散发鲜味,这尾小鱼混迹在横七竖八的鱼刺里,不显眼。我看见,那是父亲吃“剩”的。
因为怕父亲和她抢着吃剩饭,母亲就把剩饭藏在锅里,她上炕吃饭的时候才端上来,有时候还说,看看我的记性,忘了一样。但有一次父亲趁她去猪圈倒猪食的时候,下炕揭开锅,把剩饭端了上来,还发动群众说,你娘还留着好吃的呢。经过父亲的煽动,我们一起把剩饭吃个精光。母亲呆呆地看着餐桌,嘴角歪了歪,使劲地咽了口唾沫。可有些时候,母亲连剩菜和菜汤都没能心安理得地吃。有时候猪进食不好,母亲就担忧,那是一家人的盼头啊。她千方百计调理,常常把剩菜汤掺进猪食,敦促它们吃干净。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总是我们吃完饭她才来吃,父亲郑重地说:因为那些小猪还没长大。这时候,大哥的眼睛红红的,颤抖着手给母亲的小酒杯添了些酒。
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们共进晚餐的,已经记不清楚,只是感觉晚餐随着母亲的积极加盟更加丰盛了,白面饼子时不时地端上来,有时候还有炖肉。我问母亲那些剩饭呢?母亲说放进猪食里了。我懵懵懂懂地问母亲,怎么现在不着急喂猪了。母亲笑而不答。
成家之后,常常跟老公回农村的婆家,婆婆不怎么说话,就喜欢张罗一大桌饭菜。可饭菜上了桌,她却挎起个篮子说去菜园看看,只有等饭几乎凉了她才挎着一星半点菜回来。菜园就在旁边,我们几乎整个上午就在菜园里,还有什么比吃饭还重要而可看的呢?开始我认为她是担心我这新媳妇怕羞,不愿意跟我一起吃,心里还暗笑,什么年代了,我吃饭还会怕羞?可一年年,新媳妇熬成了老媳妇,婆婆还是这样。有一次吃饭时,她又要去菜园,我有些烦躁地说:都是什么习惯,不吃饭往外跑,菜园有什么非去不可的事呢!婆婆踌躇着讪讪地说:这就回来。
老公表情沉重地悄悄对我说:以前穷,上有老下有小,饭不够吃,她就磨蹭到最后吃,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富足了,她还是改不了。我愣在那里,突然间觉得揭开了多年前的一个谜底。想起大哥红着眼睛为母亲的小酒杯添上那一点酒,内心一凛,我懂得母亲竟然这样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