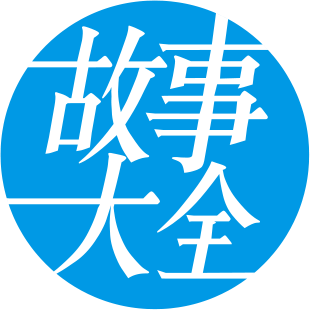记忆深处的那些少年们
那时候同桌留着最好打理的寸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我总觉得男生留寸头才最帅。
没有变声的年纪他有好听的童声,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被拉去参加大合唱的训练,我边上体育课边从窗外看他看黑板认真唱歌的样子。
他笑的时候,露出像大白兔一样可爱的门牙,肩膀会轻颤;一感冒,会和我一样一张又一张地费餐巾纸;过生日,他会送我贺卡,上面认认真真写着生日快乐,开头毕恭毕敬用的是您;无聊的时候会偷藏我的笔袋,我后知后觉,他等不及了会问,“你看你笔袋呢?”
上着课,我的右手肘就会超过三八线,霸占的地方也越来越大,我自己是浑然不觉。
可是讲台上的老师却看不下去了,老师一提醒,我才发现,同桌像个小媳妇似的憋屈在桌子的一角。我“唰”地把手肘收回来。因为我经常越境,所以我和同桌是没有三八线的。
那时候在课堂上抄词语,人还是小小的,伏案的时候整个人都埋在桌上,右手握笔左手按纸,腰板要挺直,时刻像个保卫边疆的战士,警惕着老师的查岗。
老师在班级里巡视着,兜兜转转,我瞄到老师远了,就忍不住侧头和边上的战士对话,交流交流站岗的心得体会。一边聊着昨天晚上的动画片,一边一笔一划在田字格上写下一个“个”;一边争论着几个铁胆火车侠里到底谁才是最厉害的,一边把卷起的页脚压平。如果感觉到老师的探照灯,我们就默默低下头,浑身散发着“我在写作业”“我是好孩子”的气场。两个小孩,笔不停挥,叽叽喳喳扭头讲话,两个人的脚都搭在桌子前面两个腿的杠上,摇啊摇。
冬天的早晨,阳光投到他的桌子上,在他的桌上辟出一片亮闪闪的湖泊,他一半脸被阳光照亮像是带上了半张金色的面具。我喜欢趴在桌上,看光束里的尘埃旋转飞舞,看湖泊里遨游的阳光,看他的头顶生出光圈。
我有一段时间喜欢讲自己编的鬼故事,我坐在座位上,边上围了一圈同学,坐着一层、站着一层、跪在桌上一层,我不仅自带音效还连手带脚比划着,听见他们发出“啊”“哦”和抽气声我就特别得意,好像自己和站在领奖台上的奥运冠军也没什么两样,同样接受着崇敬的目光啊。
没想到的是,班主任从后门进来,一下就惊退了我们这群乌合之众,听故事的同学再次受到惊吓立刻作鸟兽散。因为同桌错过了我开讲的时间只能在外圈抢了个位置,一眼就被班主任看见,并毫无根据地认定他聚集一堆人在商量什么坏事。
放学后,我在走廊上,看着他拉拢着脑袋从办公室出来,把早上省下的饼干塞给他,他推还给我。他看见我询问的眼光,硬是拍了拍胸脯:“男子汉嘛,虽然不是我干的,但是我也当了!怎么说我也蹭着听了不少。”“那啥,老班没怎么你吧?”“他能怎么我呀,不就是打扫一个礼拜教室嘛。”“啊?”“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让你干的,我一人就行啦。但是…….”“嗯?”“你再给我一个人讲一次呗,后面怎么样了?”
他挠了挠后脑勺,又露出大白兔似的招牌笑容,我使劲地点了点头,看见他身后的云朵被夕阳晕染,像打翻了的颜料,红的紫的美不胜收。我怀着满心满意的愧疚跟在他后面,路边樟树上的麻雀从这棵跃到那一棵,身后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
兔子瘦瘦高高的,白衬衫,牛仔裤,单肩包,斜倚在走廊上,就像是从漫画里拓下的场景。我喜欢叫他兔子,因为他白白的,消瘦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尤为突出,清澈明亮,就像浑身雪白的小兔子眨巴着大眼睛求你投食。刚升入初中,我就发现了他。
兔子那时坐在我旁边的一组,隔着一条走廊。他的位子正好是我的斜前方,每次他转过头和他后面的女生说话我就能看见他。平时他很少说话,也不跟别人交流,转过头最多就问“作业是什么?”“老师刚刚讲了什么?”
下了课,别人都奔向小店买东西或者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兔子只是静静地呆在座位上,什么也不做,既不说话也不看书,看起来也不像思考人生啊,他究竟在做什么呢?好奇心爆棚的我总是偷偷地观察着。观察观察着,就有些暗暗气恼起来,他也太淑女了吧,怎么这么安静呢。
妈妈出门时对宝宝说“你要乖乖的,不要乱动哦”,他就是那个只会四处张望绝不乱动的乖宝宝。有一次无聊在家翻字典,看到一个词“娴婳”,他的形象毫不犹豫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使劲甩头,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还是挥之不去。
初一运动会,兔子参加了五千米长跑。作为工作人员的我看到比赛名单的时候就震惊了,“他能长跑?”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当我看到橘黄色的跑道上,那个白色的身影轻轻松松地超过一个又一个对手,我觉得兔子更像是一只轻快的麋鹿,它在女王没有做梦前纵情自由地在森林里奔跑着,跨过淙淙的溪流,跃过开满野花的小丘。
我看着他的身影,又高兴又担心,左手握着半杯水,右手拿着蘸好水的棉花,从操场这端跑到那端,找时机递给他。每次我刚赶过去,他就又跑到另一边去了,我从没实行的跑步计划是不是应该启动了。
我等在那,终于他放慢速度伸出手,我连忙把棉花给他,他皱了下眉,我又赶紧递出了水,他边跑边仰头把水灌下去,只看见他喉结在颤动,有一些水顺着嘴角流到脖子。我等着他把杯子还给我,就拼命跟着他跑,他的额上眉梢鬓角都挂着汗珠,阳光照耀下像一颗颗钻石。他的脸色更苍白,但是眼睛里的光却更亮了,跟了一阵他才像发现什么似的把杯子塞给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运动会后,我们终于能说上话了。我问他,你为什么长跑这么厉害,他说,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啊,爸妈说要多锻炼;我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报体育生啊,他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
有一次因为什么事情我和他打赌,结果我赢了,当时我说我想要一大把棒棒糖。说完也没当回事,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一到教室还没有放下书包就向我走来。一贯的白衬衫,一小撮头发倔强地翘起,走路的时候带起一阵好闻的有洗衣液味道的风,他慢慢靠近,靠近,脸慢慢变大,停住。这时,我才猛地回过神来,向后一靠,后面的桌沿硌得我骨头疼。
他站着,我坐着,总觉得他从高到下已经一眼把我望到底。我的眼睛不停向他发射着大大的问号,可是他好像没有要开口说话的意思,左手往裤子口袋里一插,掏出一把棒棒糖往我桌子上一堆,右手一把,又一堆,然后转身回自己的位置。他坐到座位上,若有所思地转头看向我,半晌冒了句“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味的。所以里面什么味都有。”“啊?哦哦。”说完他又撑着脑袋“思考人生”了,我瞥了眼他的侧脸,就赶紧快乐地收拾糖了。
每一个女孩心里都有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 ,无论是你已经结婚生子还是垂垂老矣时,他都会在记忆里对着你腼腆地微笑;会在拐角处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轻轻挥手和你打招呼;他戴着耳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看见你在面前张牙舞爪,会摘下耳机,问:“你说什么?”
有句话说,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重要的胖子,对我来说,这个位置无疑是为维尼留的。
维尼有心脏病,先天性的,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爸妈才特别宠他,把他喂肥了吧,但除了这个我没有发现我们有什么不同。
他不喜欢学习,但是做事却特别靠谱,比如一起做值日的时候总是质问我:“你会扫地吗?”然后“噌噌噌”把我负责的区域里的垃圾收拾了,那叫一个快准狠。所以我叫他维尼,像小熊维尼一样,一个可爱又靠谱的胖子。
相识也是在初中,但是真的熟起来却是中考之后。初中毕业后,我们就各自飞到不同的地方了,普高,职高,技校,哪都有我们的人。我去了市里有名的中学,他去了同样“有名”的技校,学业繁忙大家又不在一起,和老同学碰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可是不知怎的,周末寒假暑假却总能和维尼碰面,直到现在大学的假期,只要回家了,我们就要滚出来碰头。
一个夏天的晚上,维尼骑着他那辆宝贝单车从远处驶来,我站在桥上吹风,他在我面前一个漂移刹住车,得瑟地瞅了瞅我,我缓缓摇了摇头表示我的不屑,继续看我的河吹我的风。
他也不生气,把车靠在桥栏上,挨着我,脚踩在栏杆最下面比桥面稍突起的地方,双手抓着栏杆,身体卷着像一只大虾,当时我想:这么大一只虾,嗯,要油爆的好了。江南小镇,四绕八绕的到处有河,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无数条蜿蜒的小河中的一条。纳凉的人已经渐渐回去,他们还要收看黄金时段的情景剧,慢慢地,行人也不多了,而昏黄的灯光依旧执着地亮着。
我们就这么呆着,不说话,吹着带着水汽的湿润的风。还好,在这一隅,还有没被都市灯光掩盖的星星,我琢摩着这一堆是什么星座那一颗是什么星星,最后琢摩出来的,也只有北斗七星。风吹了很久,星星看了很久,他突然从一个卷着的大虾变成了直直的蟹棒,说了句“等我一下”就踩着脚踏车甩出一个匆匆的背影。
回来时,他的脚踏车头的两边多了两袋东西,是两块西瓜,维尼说:“这好景好风的好夏天,怎么也不能少了好吃的西瓜啊。”于是,我们俩就在桥上啃起了西瓜,冰镇的西瓜特别凉也特别甜。维尼边吃着,边开口说:“我告诉你啊,你是不知道……”然后就是他们学校的各种奇闻轶事。我边听着,边看河里的鱼儿偷偷地冒出头,搅起一圈圈涟漪。
“喂,懒虫快起床啦,老地方吃面啊。”睡意朦胧的我抓起电话还没意识到他在讲什么,耳朵里就马上传来嘟嘟的忙音。我顿时怨念四起,这家伙到底抽什么风,说了啥啊。怨归怨,我还是老老实实起床了,趿拉着拖鞋刷牙洗脸换上厚厚的羽绒服出门,在关门的一瞬间想起来没拿钥匙,又风风火火抓起钥匙关门下楼。
裹着围巾搓着手走在路上,远远就能看到奥灶面馆门口升腾的热气,在冬天的清晨瞬间给人一股暖流,好像有人在你的怀里塞了一杯热呼呼的奶茶。
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坐在里侧的维尼,他的面刚上桌,维尼使劲向我招了招手,“你怎么这么磨蹭呢?”我还来不及分辩,就被刚出锅的大排面的香气吸引了,连忙叫道:“爷叔,来一碗大排面!”
我抽出桌上筷笼里的竹筷,两只筷子互撮着,看了看维尼的鸭腿面,说:“你怎么老吃这个啊?”他停了吸面,抬起头白了我一眼:“你还不是每次都是大排面?”面馆里人很多,木头桌子旁快速地换着人,有老人有孩子。原本风尘仆仆来的人,都从这吸收了温暖步履轻快地离开;悠闲而来的人悠闲地吃完面又悠闲地离开。
这家奥灶面馆开在街道上并不显眼的位置,店面也很小,招牌都被一年又一年的雨水和阳光打褪了颜色,但是,却像个温暖的驿站,温暖了许多人寒冬里颤抖的心,至少,我和维尼都是这样觉得的。
那些少年们,贴着不同的记忆标签,安静地坐在我的火车车厢里,火车驶过一站又一站,经过一处又一处风景,他们不会下车不会离开。
即使岁月蹉跎我会年华老去,他们也依旧是年轻的模样,在记忆的深处向我招手,一副美好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