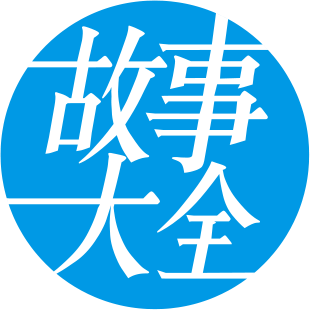母亲的大碗
那时,乡人吃饭用三种碗,大、中、小。三种碗都属粗瓷,它们造型不规整,挂釉潦草,颜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绘有蓝色潦草的图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边用麻绳样的图案收住。黑釉碗则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还透着暗红。
中号碗用途最广,乡人吃饭多用它。小号碗属于孩子,容量是中号碗的一半。大号碗的容量是中号的两倍或更多,人们管这种碗叫钵碗,家里的壮劳力吃饭用它,有长工的人家,长工吃饭用它,那些年我们家里是有长工的。
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专用的,且每年只用一次,就是她生日那天。平时这只碗被倒扣在碗橱一个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是一只白釉、蓝花钵碗,碗身就绘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图案,碗边是随处可见的麻绳图案。
母亲生日这天,家人才注意到这碗的存在,确切地说,当母亲端起这碗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了。
这时的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捧出这只大碗,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换个大碗。”然后不声不响地把锅里的饭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刚劳作过的灶前,呼呼吃起来。那时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着她那张平时就显黑的脸,脸上只是一派的满足,神情十分悠闲。
没有人去向母亲祝贺,几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姐姐,只是站在厨房门口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母亲生日的祝福,我们不会。那时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对于母亲来说,有别于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她少言语,多劳作,负责全家人衣食的运转:棉花由花朵变成布,再变成衣;粮食由谷粒变成面粉,再变成饭。
有着一双“解放脚”的母亲从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于是院中的各个角落就会传出风箱声、织机声、刷锅声、叫鸡声、叫猪声、棒槌的捶布声,直到晚间的纺车声。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这当然是催我上床。“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是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也许正是因了母亲那简短的吩咐和呼喊,我们做子女的才心领神会,无条件地接受着、执行着。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鲜少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
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物,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每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仞大锅里怎样去对待它们。家中小煎锅倒有,平时缺乏炉灶配合,只在春节时才立灶生火。
我父亲说话幽默,便过来“打圆场”,他对我奶奶说:“娘,鱼这物件怎么做也是个鱼味。”
鱼的风波总会过去。母亲还是会把做好的鱼送给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奶奶面无表情地撕扯着它们,嚼着。日子还在继续。
母亲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每逢母亲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树都在开花。
有一年母亲没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农村大变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会各阶层要平均,富户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运转折。
懂得政治的父亲率先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献了出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深挖浮财”的运动又在继续。“浮财”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宝贝。“挖浮财”要拿家中的女人说事,这种女人被称作“富婆”。政策决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来,让她们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当属奶奶了。
一天,当持枪的民兵要带走奶奶时,母亲站了出来,她对来人说:“我去吧。”她边说边向门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亲便被带到村中一个大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着十几名“富婆”。各家的饭要由各家去送,这时奶奶才取代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艺烧火做饭,送饭的任务则落到我的头上。
奶奶把稀薄的稀饭盛入一个瓦罐,我信手从碗橱上拿下一只中号黑碗,刚要出门,奶奶把一只大碗递过来说:“用大碗。”这是母亲的大碗,我后悔自己没有想到。
我低头走过大街去给母亲送饭,躲避着村人的目光,不知不觉想到一出戏里的唱词:“天无势星斗昏,地无势草无根。君子无势大街上混,凤凰无势落鸡群。”此时,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作落魄的君子和凤凰。
走到“牢”门,经过检查,我从“号”中喊出母亲。我看母亲在一个背静处吃饭,她把饭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问:“你想出来的?”
我说:“是奶奶。”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那饭很稀,先前我家做饭用两升米,现在用半升。
母亲饥不择食地呼呼喝着,我看着母亲少有的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
我大哥是谁?他自抗战初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十几年后,我问大哥:“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过上另一种生活了,便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的病症。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后,由省城回家奔丧,才发现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来了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要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不仅是父亲,也是全家人的心愿。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这一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没有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