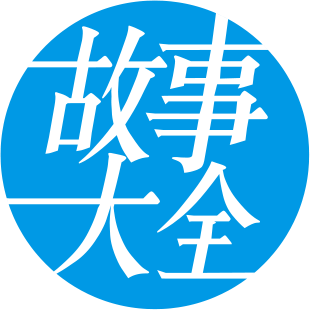她是一个废物_安徒生童话故事
镇长站在敞开着的窗户前,他身上穿着高领硬袖的衬衫,衬衫前襟上别着一枚胸针。胡子刮得光光的,那是他自己刮的,只割破一个小口子,他已经在小口子上贴了一小片报纸。

“听着,小家伙。”他叫道。
这个小家伙并非别人,就是洗衣妇的儿子。他恰好走过这里,便恭敬地脱下头上的便帽。那顶便帽的帽檐已经折断,可以塞进衣服口袋里去。小男孩衣着简朴,却干干净净,破的地方全都缝补得整整齐齐,脚上拖着一双木屐。他站在镇长面前,样子诚惶诚恐,如同站在国王面前一样。
“你真是个好孩子,”镇长说,“你是个礼数周全的懂事的孩子。我想你母亲大概在河边漂洗衣服,你快把兜里装着的东西给她送去吧,你母亲的老毛病改不了啦!
你带了多少呢?”
“只有半斤。”小男孩说道,他害怕得嗫嚅了半晌才低声说了出来,声音还颤抖着。
“今天早上她不是已经喝过这么多了吗?”那人刨根究底地问道。
“不是的,那是昨天的事情。”小男孩回答道。
“哈,两个半斤不就成了整整一斤啦。她真是个窝囊废!这个阶层的人真是可悲!
去对你母亲说,她应该为自己害臊才是。你可不要再变成一个酒鬼,不过你一定会的。可怜的孩子,你走吧!”
小男孩便移步走开去。他把便帽拿在手里,听凭他的满头金发被风吹得飘拂起来,一绺绺地竖立在头上。他顺着大街走了一段,然后拐进一条小巷,走到了河边。他的母亲站在河水里的洗衣凳旁边,用一根粗大的木杵拍打着沉重的亚麻布床单。河水滔滔流过,汹涌而湍急,因为磨坊的闸门已经打开了。急流险些把床单冲走,把洗衣凳掀翻,洗衣妇人用足了力气才把它们按住。
“我差点儿被水冲走。”她说道,“你来得正好,我要来点东西鼓鼓劲,在水里泡着真是冷得要命,而我已经在冷水里站了六个钟头了。你给我带了点什么来吗?”
小男孩赶忙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酒瓶,他母亲迫不及待地把瓶口凑到嘴边,喝了几口。
“哦,真是顶用,真是舒服,浑身都暖和过来了,就像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样,再说价钱也不怎么贵。喝一点,我的孩子!
你看上去脸色那么苍白,穿得又这么单薄,你冻得直打哆嗦。现在已经是秋天啦,河水冰凉冰凉的,但愿我不要病倒才好。不会的,我不会生病的!
再让我喝上一口,你也喝一点,只许喝一小口,不过千万不许沾上这个癖好。唉,我可怜的孩子!”
她说着就绕过小男孩站着的踏脚石走上岸来,河水从她腰里围的灯芯草围裙上,从她的裙衫上滴滴答答地流下来。她说道:“我拼死拼活地干活,洗得两只手的指甲缝里快要流出鲜血来了。但只要我能光彩体面地把你拉扯成人,吃这些苦都算不了什么,我亲爱的孩子。”
就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年岁比她更大的女人。她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瘦得皮包骨头,有一条腿是瘸着的,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一绺拳曲的假发垂在这只眼前,大概想要遮挡住瞎眼,却反而使得这一缺陷显得分外醒目了。她是那个洗衣妇的朋友,邻居都称呼她“一绺鬈发的瘸大娘玛伦”。她说道:“唉,你这可怜的女人,干起活来连性命都不顾啦,就那么一直站在冰凉的水里。你真是要喝点什么暖暖身子才行,可是你喝了那几口就有人说三道四讲你的坏话!”
于是玛伦便把方才镇长对小男孩说的那些话一五一十地全都讲给洗衣妇听,这些话当时恰好全都让玛伦听在耳中。玛伦听得直生闷气,因为一个堂堂的大男人竟然去对一个孩子数落他母亲的不是。让她更恼火的是镇长居然有脸去指责洗衣妇喝的那几口酒,而就在那天晚上,镇长自己要举行盛大的晚宴,宴席上有的是整瓶整瓶的美酒佳酿。“都是好酒,还都是烈酒!
在酒席上,许多人都会拿酒当水来解渴,可是他们却不把这叫做酗酒。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你却不行!”
“镇长真的对你这么说来着,孩子?”洗衣妇问道,她的嘴唇抖动得很厉害,“你真是有一个窝囊废的母亲,也许他的话一点不错,可是他怎么能对着孩子说呢。他们家真是让我吃够了苦头。”
“可不是,想当初镇长的父母都还活着住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那个宅子里帮佣了。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打那时起连盐都吃掉了不少,所以那些人口渴得不行,非要猛喝一通哪!”玛伦笑了笑又说,“镇长家今天晚上仍旧照样大摆宴席,其实这次晚宴本来应该推迟才对,不过消息来得太晚,酒菜都已经做好了,再要改动也来不及了,这是宅子里的男用人告诉我的。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来了一封信,说是他们最小的那个在哥本哈根死掉了。”
“死啦!”洗衣妇失声惊叫起来,脸色陡然变得像死人一般苍白。
“是呀,怎么啦,”玛伦说,“你用不着那么伤心难过。你一定同他很熟,是在那个宅子里帮佣时候认识他的吧?”
“他真的死了吗?”洗衣妇说,“天哪,他是那么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像他这样的好人还真不多。”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淌下了面颊,“哦,天哪,我的上帝!
我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那是因为我把那瓶酒都灌了下去,喝得太多,超过了我的酒量。我觉得浑身难受!”她赶紧将身子靠在木栅栏上。
“天哪,你的脸色真是太难看了,”那个老妇人说道,“我最好还是把你送回家去吧。”
“可是这一堆衣服怎么办?”
“不要紧,我可以收拾掉的。来吧,你扶着我的胳膊,孩子先留在这里照看一下,等我回来把剩下的衣服都洗掉,已经没剩多少了。”
洗衣妇的两条腿在止不住地颤抖着。
“我在冰凉的河水里站得太久了,从大清早起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不管是干的稀的都没有下肚。我身上滚烫滚烫,像在发烧一样。哦,我的耶稣,帮助我回到家里去吧!
我可怜的孩子。”她哭泣起来。
小男孩也不禁哭起来。过了片刻,他就独自坐在河边,坐在那堆湿漉漉的衣服旁边。那两个女人慢慢吞吞地走着,洗衣妇脚步踉跄,一步一冲的。她们穿过小巷,拐到大街上,走过镇长的宅院。她刚走到镇长家的大门口,便一个踉跄倒了下去,跌倒在镇长家门口的踏脚板上。路上行人纷纷围了上来。
瘸腿的玛伦赶紧跑进院子里去求救,镇长和他的客人们都站到窗前向外张望。
“哦,是那个洗衣妇呀!”镇长说道,“她大概馋酒馋得过头啦!她真是个窝囊废。她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儿子真命苦,我倒是很心疼那个可爱的孩子。他的母亲真是个窝囊废!”
洗衣妇终于恢复了知觉,她被送回到自己那个贫苦寒酸的家里,躺到了床上。好心的玛伦给她倒了一杯加了黄油和白糖的热啤酒,因为玛伦相信这是最好的灵丹妙药。然后玛伦回到河边洗衣服的地方,把剩下的衣服洗了一遍。她只是马马虎虎地洗了一下,把衣服在河水里浸了浸就捞起来扔在筐子里。
天黑时分,玛伦坐在洗衣妇的一贫如洗的家里陪着她。玛伦从镇长的厨娘那里得到了两只烤得焦黄的土豆和一块肥得流油的上好火腿,小男孩和玛伦便享用起来,那个病人闻着浓香也很高兴地说道:“闻闻这香味,就可以滋养身体了。”
小男孩上床睡觉了,他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不过他是挨着母亲的脚后跟横在床头的。他身上盖着一条用蓝色和红色碎布条拼缀起来的铺地的旧地毯。
洗衣妇觉得好了一些,热啤酒使得她身上有了点力气,美食的浓香也使得她舒服得多。
“多谢你这个好人。”洗衣妇对玛伦说道,“等孩子睡熟了,我要把这桩事情的前后经过全都讲给你听。我觉得这会儿他已经睡熟了。你看看他长得多么可爱,多么福相,两只小眼睛闭得紧紧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在怎样死撑活挨地苦度日子啊!
但愿上帝开恩,决不要让他再过这种苦日子……这桩事情发生时我正在枢密顾问官——就是镇长的父亲——家里帮佣。那天他们家的小儿子从大学里回来了。那时候我年纪轻,有点疯野又爱热闹,可是规矩老实从不越轨,我当着上帝的面都敢这么说。”洗衣妇说,“大学生性情开朗,那么关怀体贴人,他身上每一滴血都是正直善良的,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他是这个宅第里的阔少爷,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女用人,可是我们两心相许,真心诚意地相爱了。在两个人真心相爱的时候,亲吻拥抱并不是什么罪孽。他把我们的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因为对他来说,母亲就是人世间的上帝,再说她是那么聪明,那么和善。
“他走了,动身之前把他的金戒指戴到我的手指上。等到他刚离开家门,我的女主人就把我叫到她跟前去,她讲话十分认真严肃,却又和颜悦色。她不厌其烦地向我解说他和我之间在智力和身份上的差距有多大。‘他现在只看到你长得有多好看,可是美貌是很快就会消逝的。你没有像他那样的学问和教养,你们两个人在精神的王国里是毫不相配的,这就埋藏了不幸。我十分尊重穷人,’她又说道,‘到了上帝面前,也许一个穷人会得到比许多富人更为荣耀的位置,可是在世上做人却有一定的规矩,就像行车上路那样,不可以越轨走错了道,否则就非翻车不可,而你们俩的结果便是翻车。’
“女主人接着又说道:‘我知道有一个很有气概的男人曾经向你求过婚,那个手艺人是做手套的师傅埃里克,他是个鳏夫,没有孩子,家境挺不错的。你不妨再想想吧。’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刺穿了我的心,可是她说的话句句在理,一点不错。她的话使我十分痛苦,这些话的分量把我完全压垮了。我亲吻了她的手,流下了许多苦涩的眼泪。我一回到我自己的房间里便扑倒在床上,眼泪更是哗哗地流淌下来。
“那个晚上真是漫长而沉重啊,上帝才知道我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和怎样苦苦挣扎。到了星期天,我就上教堂去,到圣坛前祈求上帝给我指点迷津,就好像是天意一样,我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候,迎面来了做手套的师傅埃里克。我们这么一照面,我心里就不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两个在身份地位,在境况条件上都很相配,何况他还是个手头上相当宽裕的人。于是我径直朝他走了过去,拉住他的手问道:‘你对我的心思仍旧没有变吗?’‘是的,永生永世都不会变。’他说道。‘那么你情愿娶一个尊敬你、钦佩你却对你还没有什么感情的姑娘为妻吗?
当然,说不定那个姑娘有朝一日会喜欢上你的。’‘爱情迟早会来的。’他说道。于是我们订下了婚约。
“我回到了女主人的家里,他儿子给我的那个金戒指我一直贴胸藏着,白天我不敢把它戴在手指上,等到每天夜里我躺到了床上,才能把它戴上。我不断地亲吻着戒指,直到我的嘴唇都磨出血来。后来我终于把戒指还给了我的女主人,并且对她说,下个星期天牧师将在教堂的布道坛上发布我和埃里克的结婚公告。于是女主人伸出双臂把我搂在怀里,连连亲吻着我,她没有说过我不中用,大概那时候我干起事情来还挺利索的,要比现在强得多,再说我还一点没有尝到人间的艰辛。我们就在二月二日圣烛节那一天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一年日子过得很顺心,我们有个伙计,还有一个学徒。玛伦,你就是那时候到我们家来帮佣的。”
“是呀,你是个随和善良的女东家。”玛伦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和你男人对我是多么好。”
“你来的时候正是我们家日子过得最红火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没有生孩子呢。至于那个大学生,我再也没有同他见过面。噢,不对,我见到过他一面,可是他却没有瞅见我。他回到老家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我看到他站在母亲的坟墓前,脸色铁青、苍白,那么伤心悲哀,是因为他母亲去世的缘故。后来他的父亲也死了,他没有回来送葬,那时他已去了国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知道他终身未娶,听说他当上了检察官。他大概早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就算他见到我,恐怕也不会认出我来,我变得那么难看了,不过这也挺好。”
接着她又讲到了她经历的苦难:不幸一下子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手头上攒下了五百块银币。那时大街上有一栋房屋要出售,卖价二百块银币。这个价钱十分划算,很值得把它买下来,拆掉之后再盖一栋新房子。于是他们便把那栋房子买到了手,请来泥瓦匠和木匠,估算出营造新房子的费用,总共还要花一千零二十块银币才能再盖起来。埃里克借到了一笔贷款,那笔钱是从哥本哈根借来的,可是把那笔钱捎过来的船长偏偏就在这次失事中遇难,连人带钱一起沉入了海底。
“那时我刚生下这个可爱的儿子,我丈夫当上了父亲,可是却染上了重病,一下子躺倒了,有八九个月光景我天天要为他穿衣脱衣。我们手头上的钱花得光光的,只好去借了又借,背了不少的债。我们家里穿的用的全都变卖掉了,可是孩子他爹也没有活下来,抛下了我们母子俩。
“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拼死拼活地苦干,为的是养活儿子。擦洗楼梯啦,洗衣服啦,不管是粗活细活,什么都干,可是我的日子却一点也没有好起来,不过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有什么办法?
反正上帝早晚都会让我得到解脱的,但愿这个孩子不要被遗忘,不要没有人照管。”
说完,她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觉得自己好多了,她相信自己有力气可以去干活了。可是当她一踩进冰凉的河水的时候,就猛地一阵眩晕,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的双手痉挛般地朝着空中乱抓乱舞,她又向前迈了一步,便不由自主地栽倒下去。她的脑袋仰在河岸上,可是两只脚却浸泡在河水里。她脚上穿的那双木鞋被河里的流水冲走了,那是她站在河里干活时穿的,每只木鞋都用一束干草系在脚上。直到玛伦到这里来送咖啡给她喝的时候,才发现她倒在河边。
就在这时候,镇长派人来传了个口信,叫她马上前去见镇长,镇长有要紧的话对她说。可惜已经太晚了。大家找来了一个剃头师傅给她放血也无济于事了,洗衣妇已经死去。
“她是喝酒喝得送掉了性命。”镇长说道。
在传递镇长弟弟死讯的那封报丧信中,还写明了死者的遗嘱,遗嘱中说,要留给那位曾经给死者父母当过女佣的手套匠人遗孀一笔钱,数目是六百块银币。这笔赠款应按照实际的需要,拆成大小若干份,分期支付给那位遗孀或者她的孩子。
“我弟弟曾经同她有过点什么交情吧。”镇长说道,“如今她总算不在人世了,那倒真是件好事情。那个男孩子可以得到那一整笔钱。我会把他交给正派本分的人家去抚养,他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手艺人。”
上帝赐福吧。
镇长把小男孩叫来了,答应照管他,还告诉他说,他母亲死了要比活在人间好,因为她是个没有用的窝囊废。
洗衣妇埋葬在教堂墓地的义冢里,那是埋葬穷人尸骨的地方。玛伦在她的坟上种了一株玫瑰,小男孩站在她的身边。
“我亲爱的母亲,”小男孩说道,他的泪水如泉涌一般地流淌下来,“难道是真的吗,人家都说她是个窝囊废!”
“不,她才不是什么窝囊废!”老妇人玛伦说着抬起头来仰望着头上的苍天,“多少年来我一直心里很有数,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夜让我更加明白过来。我对你说:她是个可敬的好女人!上帝也会赞成的,尽管别人说她是个窝囊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