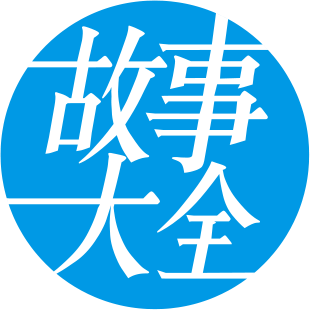魏晋风流甲天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时期,出了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但正是有了这段历史和这些人才使中国的文化显得熠熠生辉,丰满动人。

那是一个多事之秋,三国纷争,八王之乱,十六国逐鹿中原……在那个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岁月,政治高压、思想禁锢的年代,多少名士俊杰报国无门,反引来杀身之祸。于是清淡之风应时而生,儒道佛三家互为交融,学术思想被推入又一个高峰,虽然少了许多经世济国的良才,却多了一群才思风流的高士。“魏晋风流”凝成一种独特的风格,照亮了历史,也影响了后世。
“魏晋风流”是一种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兼“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于一体,用言行、诗文、艺技等方式使人生艺术化。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就是具有这种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他们颖悟、旷达、真率,不为名教所缚,不为礼法所拘,虽然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的本真与性情。这是一群游离儒家道统之外,却又主宰了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精神的大人与思想的巨擘!
随着汉朝君主统治的日益加强,儒术独尊之后,儒学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繁琐的训释加上谶纬神学的迷信光圈,紧紧地禁锢着士人的思想,而外部的纷争也加快了腐朽王朝的崩溃。所谓“时势造英雄”,在这样的乱世中,一些有志有识之士发挥作用,他们像惊涛骇浪一样冲击着朝廷的陈腐和丑恶,以陈蕃、李膺为代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与汉代统治思想大相径庭的新精神、新人格,为魏晋清谈名士的出现,新风度的建立健全,起到了先驱启蒙之作用。陈蕃对强权的抗议,李膺对宦官的打击,引发了“匹夫狗撸κ亢嵋椤钡睦顺保似鹌菲拦洹⑴勒治的风气。历史上称之为“女幸(左女后幸)直之风”。这时的清议已经是清谈的开始了。然而庶人自由议政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在所难免,一场“党锢之祸”酿造了名士的悲剧。李膺、杜密、朱寓、刘儒、范滂等百余人惨死狱中。党人清议虽被镇压,但黑暗的政权愈发激起了人们强劲的结党议政的浪潮。而另一边,一批守死善道的儒士们却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对抗朝廷。如郭太、徐孺子等。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郭太深谙其中道理,于是他退出政治,闭门教书,培育了一大批才子学士,并带领他们走上一条较为安全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可以不与朝廷合作,在讨论学术中发泄愤懑,在教育士子中发挥作用,以完成善德与善道的理想,实现儒士的社会价值。《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禁锢了的清议,不得不开始转向,另求出路,其结果是清议转而为清谈……其间转向契机,实应从郭林宗讲起。郭虽善人伦,而不危言核论,实开清谈之风。”政治的高压与黑暗,儒家的涣散与解体,道家的重新复苏,士人崇尚自然与性情,在这多重因素下,使得清谈兴起,玄学滥觞。
慷惯磊落的建安风骨
“魏晋风流”自“建安风骨”开启,以曹魏集团的“总裁”曹操为揭幕人。作为一代文学家,曹操以其卓绝之才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明诗》篇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建安时期是才人辈出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名士,他们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慷慨悲凉、骏爽刚健”之风格,史称“建安风骨”。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其代表。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曹操当年征讨乌桓,凯旋经过昌国时所作的名篇《短歌行》,诗中歌咏了他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名士的渴求与友情。当时名士地位和清议人物权威日益增高,曹操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威望,自不敢小觑名士。在曹操穷困卑微时,他得知许劭清议名望甚高,便常带上厚礼讨好许劭,请求他为自己做些评论。许劭向来鄙视他,便给了他一句:“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却闻言大喜,因为自此得了英雄的称号。
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废吟咏,创作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歌。王沈《魏书》中说他“文武并施,御军十余载,手不释书……”钟嵘《诗品》中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在《蒿里行》诗中曹操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只是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曹操的诗作中并不多见,曹操的诗更多体现的是建功立业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步出夏门行》便是其代表作。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二解“冬十月”、三解“河朔寒”,写归途中的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正是这种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使得曹操最终称霸天下。
曹操在诗歌上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改国号魏,为魏国的开国君王。曹丕也喜好文学,一生著有集二十三卷、《典论》五卷、《列异志》三卷。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这样评价他:“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可惜曹丕无旷大之度,终不成古之贤主,而其残害手足之行径更为后人所不齿。“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其弟曹植以诗发出对他的控诉。较之曹丕,曹植在文学上愈发显示其天赋异禀,曹植10岁余便能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几次欲立其为太子。然终因其行为放任,屡犯法禁而作罢,在曹植身上,已经初显魏晋时期名士那种厌恶政治争斗而崇尚自然率真任诞的风格。
曹植的诗歌以建安为分水岭,前后期内容迥然相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前期诗歌里充满了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及趾高气扬的意味。“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个壮志凌云的热血男儿呼之欲出。然这种风采在其后期创作中已不复可见。曹植后期的诗歌大多充满了哀怨与愤懑之情。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其内心的忧伤与痛苦可想而知。“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曹植借托怨妇之口,道出内心的凄凉与寂寞。这类以弃妇自比的诗歌成为曹植后期创作的特色之一。除了这首《七哀》外,其他如《浮萍篇》、《杂诗》等诗里皆有怨妇形象的运用。
曹植虽然仕途失意,但在文学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尤其在诗歌艺术领域取得很多创新发展。汉乐府古辞原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吾山书院记》中写道:“沿山路攀登,至‘秀野堂’,堂前洗砚池,金鳞游泳,有吐墨状……北望郁然有灵秀之气,乃‘羊茂台’。子建祠与墓傍山向西,由台向东,拾级而上,至绝顶,上有柳舒城,是曹植读书处。”相传曹植还是中国佛教梵呗音乐的创始人。魏太和三年(229年)曹植封东阿王,历时四载。初登鱼山,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鱼山顶西侧有一石壁,至今仍留有“闻梵”两个朱红大字,据记载,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闻梵”处便是曹植当年闻听梵乐的地方。曹植闻听的梵乐后来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每年,日本宗教界都有大批人士前往鱼山参拜曹植墓,并在墓前演奏曹植当年创作的梵乐。鱼山梵呗,绵绵不绝,滚滚黄河,青山叠翠,在如许一云水胜地,曹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园。而这方神仙之地也给曹植以无穷的灵性熏陶与文思启发,成就了一个遗响千年的文学家。
建安七子也是当时名重一时的高士,尤以孔融为最。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家学渊源,文才甚丰。从小就显现出不凡的才华与胆识,有“神童”之称。孔融十岁那年随父亲来到首都洛阳,当时河南尹李膺名声极大,“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后汉书·李膺传》)。但是他“不妄接宾客”,不是当世名人和通家都不获接见。而孔融还是个孩子,却偏要见见李膺,他对李府守门者说:“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请通报。”李膺请他进来后问他道:“高明(称对方的敬词)祖、父与仆有恩旧乎?”孔融答道:“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惊叹,李膺也称赞他将来“必为伟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融别传》)
孔融一生“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他虽为建安七子之首,并曾为曹丕座上客,但他始终不亲附曹操。《孔融传》中说,他在朝任大中大夫时,性格宽容,少忌好士。大中大夫本是个闲职,他就广交朋友,整天宾客盈门。他常常感叹:“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不知道在欢乐无忧生活的背后,正潜伏着杀身之祸。曹操对他的“座上客常满”极为“嫌忌”,将之称作“浮华交会”,并多次向孔融发出警告。可惜孔融没有引起警惕之心,继续“浮华交会”,就为以后的被杀埋下了祸根。
孔融虽身为圣裔,自幼习儒,但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他耿介豪纵的性格,其言论行为便常有出格之处。史载孔融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装出行。在孔融心中,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他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谁能想到竟然出自他这位孔圣人的子孙之口呢?
即使是面对权倾天下的曹操,孔融也照样直陈其害,毫不避忌。他对曹操多次以言语相讥,曹操在外表上故作宽容,内心实嫉恨很深,欲除之而后快。建安十三年(208),当时任御史大夫的郗虑和任丞相军谋祭酒的路粹,秉承曹操的旨意,罗织了孔融的四条罪名:一是有合众谋反之心;二是毁谤朝廷;三是不守礼法;四是不忠不孝。曹操根据这些罪状判处孔融死刑,并诛连全家。
一代真人就这样含冤而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然孔融扬善嫉恶,刚正不阿之风范却使他名垂千古,深受后人称誉,人们说他“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
与孔融相比,邴原却懂得守死善道,保护自己。邴原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品行高尚闻名,州府多次聘他出仕,他都拒之,而是到处游学,结交名士。后来才勉强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官,很快就又偕家归隐。公孙度称他是“云中白鹤”,说明他为人不守常规,行事常出人意表。邴原回家后,招收学生讲学,与郑玄不同的是,邴原的学说未见著作流传。可见其作风豪放自由,喜身体力行。邴原最后做了曹操的丞相征事,却非出自愿,为了自保,他装病懒散,消极应付。他的原则是不远也不近,不卑也不亢,一切以名士之道为准,率名士之性而行事。邴原为魏晋清淡名士树立了不言政事的榜样。
崇尚自然的正始之气
曹氏代汉,一个新的王朝诞生后,给汉末以来苟全性命于世的士子们带来一丝80的曙光,士人们以道家哲学为出发点,摈弃汉儒的神学思想,对儒学重新阐述,掀起了清谈热潮,促进了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发展。
从曹丕登基为帝到正始年间,正是玄学家以道释儒,儒道融合的时期。这时期突破了两汉神学与礼法禁锢,形成了一种平等自然的学术氛围和追求个性自由任诞的新人格。士大夫们亦儒亦道,陶醉于清谈与思辩的乐趣之中,至正始年间,在何晏、王弼等名士的引领下,清淡之风愈吹愈劲,震撼朝野。
正始名士可划分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中年政治实力派和以王弼、钟会为代表的少年思想家两代人。何晏、夏侯玄、王弼被公认为正始名士的三大领袖,尤其是何晏地位更是举足轻重,可谓玄学思想的创始人。有人说,如果“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极其出彩的篇章,那么何晏的风流洒脱和他的《道德论》则为这一篇章浓墨重彩地写了一个序。
何晏,字平叔。河南宛城人。东汉末年,董卓入京,诛宦官,杀外戚。何氏几乎被灭尽。惟独何晏的母亲尹氏带着还在肚里何晏顺利出逃。何晏成了何家唯一的香火。后来,尹氏嫁给了曹操,何晏也就成了曹家一个特殊的成员。何晏是个早慧之才,《世说新语·夙惠》记载,他七岁就“明惠若神”。由于何晏才华出众,不亚于曹丕曹植曹冲。曹操对这个“假子”疼爱有佳,他的地位甚至可以与作为魏王太子的曹丕相比。曹丕因此而憎恨他,在他当权的黄初时期,一直都没给何晏官做。在家族中受歧视,在政治上被冷落的何晏便潜心于《易经》与《老子》,积极地在清谈名士间逞其辩才,成为名声远播的玄学大师。史称他“好老狂言”,“善谈易老”,上承西汉扬雄《太玄》,远绍先秦老、庄“玄之又玄”而开魏晋玄学。
当时与何晏一同清谈的一批官员,有夏侯玄、诸葛诞、刘熙、丁谧等,被冠以“四聪”、“八达”、“三豫”等美称。“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这是何晏在《道论》中的一句话。何晏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即“无”。天地万物是“有所有”,而“道”则是“无所有”,是“不可体”的,所以无语、无名、无形、无声是“道之全”。何晏“无”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魏晋时期士人的思想。
明帝驾崩后,以曹爽为首的清谈名士掌权,削弱了司马懿的实力。这时,何晏任尚书,选拔了许多清谈名士,这些人在行政之余清谈论辩,著书立说,呈现百家争鸣之繁荣气象。裴秀、王弼等后进之士就在这时挤入时代的舞台,成为玄学思潮的主角。
如果说何晏是正始名士集团的组织领袖和玄学理论的创始人,那么王弼却是玄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弼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何晏后期玄学思想的变化。
王弼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汉末八俊之一王畅的后人。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史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他去拜访裴徽时,裴徽曾问他:“你说‘无’是万物的本根,是很正确的,但是孔圣人从没有讲过‘无’,只有老子反反复复地讲个不停,这是为什么?”王弼说:“孔圣人本身就体现了‘无’的德性,而‘无’又是不可解说的,所以他只讲‘有’;老子、庄子还没有脱离‘有’的境界,所以就不停地说自己所不足的‘无’。”(《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裴徽问的是现实的具体问题,王弼却从“有”与“无”的哲理高度予以解说,表现出一个少年哲人的非凡的思辩能力。但是,他只有与何晏相知之后,才真正名满天下而受到重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说:何晏为吏部尚书,既有地位又有名望,常常谈客满座。王弼当时还未成年,就慕名前往求见。何晏不以他年轻无名而拒之,热忱地接见并选了一道难题考他,本以为会难住他,谁知王弼接过题目便辩驳起来,在座的人都被他驳得无话对答。于是王弼又对换正反双方论题,自问自答,十分精彩,在座之人无不为之折服。而何晏并不因为输于一个少年而发火,反而自此以后,非常敬重王弼,当何晏完成《老子注》后,就去王弼家征求意见。当他看见王弼注解的《老子》后,十分佩服地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于是回去以后就把自己的《老子论》改写为《道》、《德》二论了。何晏在思辩水平与学术成就上虽不如王弼,但他以一个玄谈领袖的高尚人格,为学术界营造了一个自由探讨、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学术繁荣、玄学昌盛,真正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然而这股清谈玄风随着曹氏集团的灭亡而夭折了。正始十年(249)正月初六,司马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杀了曹芳、曹爽以及何晏、丁谧、李胜、桓范等名士,史称“高平陵事件”。司马懿独揽大权后,为稳定自己的地位,疯狂地杀尽曹操的后裔,无论男女老幼、出嫁女子一律诛杀,其恶行就连他的后世子孙都感到羞愧。正始名士虽然损失惨重,还被加上种种罪名,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玄学思想却征服了魏晋以后的文士,历千年而不朽。
放旷任诞的竹林贤士
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专擅朝政,诛杀异己,充分暴露了豺狼本性。司马昭继位后,其手段更为残酷,他借名教治国的旗号,压制捕杀清谈名士,在这种严酷的政局下,玄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正始时期的谈《老子》为主,转为以谈《庄子》为主,一些论题随之改变,玄学至此更为成熟。
这个时期的玄学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人物。但这七人中存在一些学术观点的分歧,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也有所差异。
阮籍系“建安七子”之一阮禹之子,他完全有机会跻身于权势之家,但他不屑为伍,以醉酒的办法避拒。据《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曾随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与之相见,本想考察一下他的才学,可是他终日一言不发,自然就没有授官给他。又一次太慰蒋济听闻他有才,召他做官,阮籍谢绝了,后在乡人们劝说下才勉强到任,不久即以病为由辞职了。曹爽辅政时召他为参军,他也称病推辞。直到司马氏当权以后,阮籍才开始出仕,由从事中郎做到关内侯、散骑常侍。当他听说步兵营人善于酿酒,便请求去做步兵校慰,在任上终日燕游,遗落政事。由此可见他虽然做司马氏的官,却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于淫威。为了自保,他经常饮酒至醉,“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钟会多次想找他茬子,都因他大醉不醒而无从下手。
阮籍之所以对权势没有兴趣,除了仕途凶险外,更主要的是他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晋书·阮籍传》说:“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阮籍任性行事,不守礼教,而追求个性自由。他家邻居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当垆卖酒,他就与朋友王安丰常去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妇人旁边。他的嫂子回娘家时,他去告别,有人讥笑他不懂礼,他回答说:“礼岂为我设也!”他在司马昭面前也是任性而为,司马昭为晋王以后自以为功德盖世,坐席严敬,只有阮籍敢于箕踞而坐,嘴里还吹着口哨。在为母亲守丧期间,还到司马昭的宴席上大吃大喝。司马昭之所以能容得下他,是因为欣赏他那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和发言玄远的作风,他的用心是将阮籍树为官员风范,从而使自己摆脱监视,为所欲为。
阮籍最爱读的书是《庄子》,其中对礼法的嘲讽,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待人世纷争、是非曲直、生死存亡的哲理,“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态度,很符合阮籍的心意。于是自正始以来的以《老子》为清淡中心的玄学,变为以谈《庄子》为中心。阮籍在庄子研究方面的建树虽不及向秀和郭象,但他却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
“学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阮籍在这首《咏怀诗》中咏出了自己对庄子哲学的理解。他认为各种物类,虽然德性不同,大小悬殊,但各有适合于自己的幸福,不必艳羡不合本性与本分的行为。这也透露了玄学家与庄子的不同。玄学家大多走的儒、道融合之路,并不弃绝人世的功名。阮籍想为社会立功而又心怀愤懑,他的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这在其著作《达庄论》中有论述),这种理想与司马氏的名教治国的现实是相抵触的。所以他在理想与现实之中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点,实现他人生的逍遥游。
这一点向秀与阮籍非常相似。不过向秀认为“无”的哲学,“无为而治”的政体,作为理想是美好的,但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向秀对庄子进行了重新诠释。向秀认为种种事物虽有大小区别,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本性所需,而且行为与自己的地位、身份、才德等物质相称,都一样的可以逍遥。在养生方面,他主张纵欲足性,甚至认为人应该求富求贵。他始终致力将自然与名教和谐地统一,因为只有这种统一才能使人的自然情性得到满足,是通向逍遥之境的起点。
在“无的哲学”上,嵇康是竹林七贤中体现得最为彻底的一个。在养生问题上,他与向秀截然相反,主张“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在对待自然与名教关系上,嵇康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相比其他六贤,嵇康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主张更为明确,其性情也更为率真刚烈。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在嵇康看来,学校是停尸房,读经是说鬼话,六经是污秽,仁义是臭腐,经常看书会瞎眼睛,学礼义会变成曲背。他以老庄的“自然无为”论、“自然人性”论去批判儒学、圣人和名教,令当时正提倡礼法的司马氏集团和拥戴司马氏的礼法之士大惊失色,惶恐不安。
嵇康不思仕途,平时以打铁为生,与朋友相交为乐。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却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钟会不理不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才开口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大怒之下,竟写下绝交书,可见其不合作态度之坚决。
后来,嵇康为了洗清好友吕安的冤屈,而卷入政治漩涡之中,钟会趁机在司马昭面前进谗,此举正合司马昭之意,于是胡乱编了个罪名杀害嵇康。
嵇康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但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就戳,时年四十。
如果说嵇康是一位越名教的战士,那么刘伶与阮咸则是浪漫主义诗人了。刘伶贪杯是世所闻名的,其饮酒纵情肆志,往往烂醉如泥。他倾心老庄,蔑视礼法,《晋书》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刘伶对世俗的富贵长寿全不在意,既超越世俗,也超越自我。他不愿像向秀与王戎那样走与名教融合之路,而坚持无为之治,自然不为当权者所接受,只能在酒中逍遥了。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尤擅音乐,常与亲友弦歌酣宴。有一次阮氏宗人聚饮,用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忽然一群猪过来饮酒,阮咸就和群猪共饮起来,由此可见其放达狂诞之程度!不过这也成为他仕途的阻碍。虽然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但不善于处理关系的他一直得不到升职。反而琴艺音律远不如他的荀勖却得权得势。阮咸内心之苦闷也是可想而知。
玄谈之风的振兴,为这些痛苦心灵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向、郭的逍遥义也成为解决这个时代难题的一剂良药。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终分崩离析,各散西东。
玄佛交融的东晋流风
公元317年,晋愍帝死,西晋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从此开始。西晋虽亡,但名士清淡之风并没有止息,玄学也没有被扼杀,反而随着东晋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这个时期的玄学开始向佛教靠扰,士人形成集儒、道、佛三家为一体的新人格。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从正始末期到西晋灭亡以前,政坛空气比较恐怖,致使许多名士利用清谈避难,在玄理中寻求精神寄托。而东晋建国伊始,有幸得到一位管夷吾式的主政者王导,使社会相对稳定。在驱除了刘隗、刁协之后,宰辅宽惠,学术自由,名士不用再提心吊胆,因而学术研习范围渐渐拓宽,对佛理的兴趣日益浓厚。佛理不仅丰富了玄学的内容,而且进一步净化了士人们的精神境界。尤其对于王导来说佛理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王导当时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北有敌国虎视眈眈,内有刘隗之类政敌暗算,接着又是苏峻之乱,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与负担自非一般,于是与高僧交流“空”“无”之道,则成为他最好的抚慰心灵之法。在王导的影响下,佛学之风渐盛,而成为一股流风袭卷了东晋朝野。
与王导齐名的另一个宰相谢安也是个清淡名士。他的处世哲学接近庄子的“无用之用”。这种哲学在社会黑暗当权者妒贤嫉能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谢安在年轻时一直敛光韬晦,隐居山林,弹琴写字,吟风弄月。他与当时的很多名士常在一起清谈玄学。有一次谢安和支道林、许询一同在王濛家聚会,论题是《庄子》中的《渔父》一篇。谢安看了题目后,便叫众人讲论,等众人全部论述完毕后,他提出诘难,并顺势自述体会。发万余言,表现出极高的思辨能力与才华。他的论述见解出众,机锋迭起,既有自问自答的风趣,又有情感气韵的烘托,浑似化作那渔父一般潇洒脱然,在座的人无不受到感染,精神为之大振。(《世说新语·文学》)《渔父》是庄子杜撰的故事,说孔子在外弹琴时一个渔父闻音前来,问子贡弹琴者何人,子贡说:“是一个为天下谋利的圣人。”渔父却摇头说:“仁爱是够仁爱了,只怕难于免祸,将劳心苦形而损害其生命的本真。唉!他离道太远了。”子贡把话转告孔子,孔子追上去虚心求教,渔父告诉他应该谨慎修身,保持本真,回归自然,方是正道。孔子闻言顿如醍醐灌顶。谢安对此深有体会,所以终身奉行的正是渔父这种珍视自身的本真原则。
还有一次,谢安和孙绰相约泛舟海上,不料起了风浪,一时间波涛汹涌,浪卷云翻,同伴都大惊失色,想要马上返回。只有谢安一个人游兴正浓,吟啸诗文,若无其事。划船的老头看他相貌安闲,神色愉悦,便继续向远方划去。直到风急浪猛,小舟像一枚树叶在惊涛骇浪间翻转的时候,其他人惊恐万状,站起来喊叫,谢安却从容地说:“如果都这样乱成一团,我们就回不去了。”大家才平静下来,船得以平安驶回。这件事之后,大家无不佩服他的胆魄,也认识到只有他才能镇安朝野。
随着谢安名气越来越大,要他出山为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可见谢安的名望之大。后来在桓温的威逼征召下,谢安无奈只得出仕,41岁的他在桓温部下任司马之职。当时朝政大权已落入桓温之手,桓温野心更加膨胀,谢安看出他的谋篡之心,与他斗智斗勇,最终未让他如愿以偿。东晋王朝在谢安的辅政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并以小胜多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王朝得以继续存在。
史载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又能顾全大局。他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这些都是谢安为人称道的品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就曾将王导、谢安并提,指出:“导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说:“安三宰天下,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这些古代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谢安的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谢家的府第车马、权力财势都随历史的烟云而消散,但谢安作为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永远地留存在史册里。
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也是东晋著名的玄学名士。“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这是苏轼赞美王羲之书法的诗,苏轼形容他的书法,像谢道蕴的风韵一样清淡娴雅,潇洒脱俗;又像天龙惊跳,遒劲多姿。在这个评价之中,体现玄学的形神并重,以形写神之原则。王羲之以其娴熟至于化境的书技,在极美的字形中,表现出一个清谈名士的性情之真。王羲之自幼便以骨鲠率真著称,长大以后,顺随自然,不慕荣利。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家选女婿,王导叫他到东厢房去看那些子弟。这位门生回去对郗鉴说:“我看王氏子弟都很好,然而听说我去选女婿,一个个都矜持起来,其中只有一人坐在东床上,袒胸露腹地大吃大喝,毫不介意,像没有听说这回事一样。”郗鉴说:“这个正是好女婿啊!”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东床快婿”之词由此而来。王羲之后来出仕在庚亮部下做参军、长史。庚亮死后,朝廷诏他任职,他都不接受。只有同是清谈名士的殷浩请他任参军、右军将军,他才接受。但由于与殷浩政见不合,王羲之很快退出官场,回到家园,游乐寄情于山水书画之间。他的书法极品《兰亭序》就是在此时写就的。《晋书·王羲之传》说:“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允、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山水的灵气陶冶了他的性情,也造就了他的书法艺术。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三国历史频道,阅读更多三国故事/历史/人物事件!